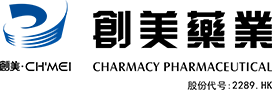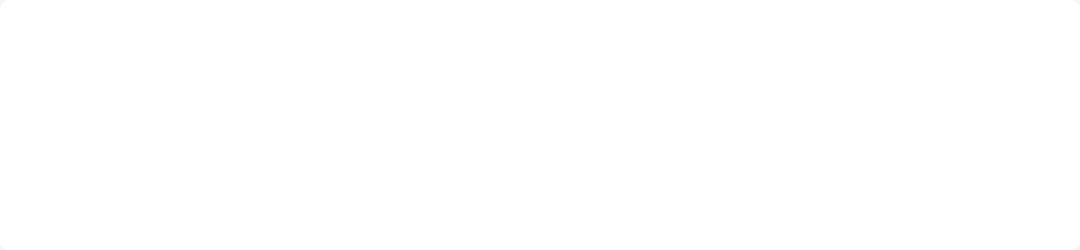来源:药链圈
随着各地“药品比价通”平台的上线,药价改革的覆盖面从院内向院外延伸。从年初的四同到年中的比价,医保改革正在向精细化推进,通过借助各类政策工具降低整体的损耗。
从表面上来看,无论是四同还是比价,拉平药价差是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一方面可以惠及民生,另一方面则可以有效降低医保的损耗,并为医保支付价的全面实施提供基础设施。但如果回到DRG即将全面覆盖以及门诊统筹这两项政策来看,药价差的治理只是整体门诊改革的一小步,未来的政策工具将会在有效控制门诊支出上发力。
由于DRG/DIP的实施,医院有动力将住院费用向门诊转移,以减轻单个病例的住院费用压力,减轻DRG带来的亏损压力。由于医疗服务无法转移,可转移的费用主要是检查和药品,主要的流向是医院自身的门诊。另一方面,门诊统筹实施之后,医疗机构和药店的门诊都将获得统筹资金报销。由于门诊的道德风险远高于住院,而且也缺乏类似DRG那样的工具对门诊进行管制,门诊费用必将大幅增长,对统筹基金形成巨大的压力。
面对门诊费用的高增长,多种政策工具必然逐步推出,比如门诊点数法、分级诊疗和处方外流等。如果从仅从药品开支的费用控制来看,处方外流本来是控费的最佳路径,因为处方流出医院之后,药店可以对处方进行替换,监管只要对仿制药替代率进行有效考核就能持续推动药价下降。但在东亚地区,除了日本采取大额补贴医生最终成功的推动了处方外流,其他经济体均没有处方外流成功的经验。
由于经济高增长期间没有采取对医生进行补贴,在经济进入平稳增长之后,不管是控制医院的门诊量还是药剂师的处方量,都很难推动医院和诊所的处方外流。不过,即使从处方外流已经成功的日本来看,其外流的处方只有22%出头来自医院,超过77%来自基层。这一方面说明基层更有意愿将处方流出,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的分级诊疗相对成功,病人的处方主要获取途径来自诊所。不过,日本的分级诊疗成功主要来自强制,病人直接去500床以上大医院就诊,病人要额外支付5000日元附加费,2018年又将门槛从500床改为400床。
而从中国台湾地区来看,由于没有对医生的补贴,处方外流主要来自基层,虽然整体的处方外流比例有36%,但医院的外流处方只有1%。而且,很多基层处方虽然外流,但都是流向指定药店,这些指定药店与诊所有着紧密的利益连接。
由于中国的基层主要收入来自药品,无论是社区卫生中心还是乡镇卫生院,其门诊药占比一般都超过60%,如果将处方外流,其门诊收入更低,依赖政府补贴将更为严重。所以,无论是医院还是基层诊所,处方外流无法成为政策调节药品开支的工具,只能采用在院内直接替换的集采模式。也就是以医院报量强制将院内70-90%的处方直接替换成仿制药。虽然政策鼓励药店参与集采,但药店需要自负盈亏,无法像公立医院那样获得财政补贴,药品价格平进平出的模式对其冲击较大。如果集采药品销售带来的流量不能转换成高毛利的产品,药店销售集采仿制药的积极性并不高。而且,由于中国没有药事服务费,药店完全依赖价差,无法使用药事服务费作为调节杠杆推动其销售低价药。
因此,在当前的市场上,政策的重点必然在医院,通过集采和国谈,有效控制院内处方的流向,从而达到药价治理的目标。但是,由于医保支付价仍然在试点,并没有全面覆盖。在公立医院之外,无论是民营医院、药店还是基层医疗机构,仍然可以在同一款药品上以更高的价格获得医保的报销。同药不同价加大了门诊统筹资金的快速消耗,四同的实施和药价比较系统的上线都是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从政策结果来看,四同和比价减少了医保损耗,拉平院内外的价格,但无法限制院外的患者选择。因此,严格限制门诊统筹资金报销的处方来源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在开通门诊统筹之后,由于原先药店一直采用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处方,其补方特性较为明显,有助于高价药的销售。所以,今年以来各地对获取门诊统筹资质药店采取了严格限制处方来源的措施,要求处方必须来自医保定点机构,而非无医保资质的平台互联网医院。这导致自从4月份以来,很多药店的客流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从目前来看,统筹药店受到处方来源的限制、药品比价和进销存一体监管,对其高标价高毛利产品的销售会形成明显影响。反而是无门诊统筹但有医保资质药店的灵活度要相对较高,但无门诊统筹资质药店面对的是医保个帐大幅减少的用户,用户的购买力明显受损。
从总体来看,医院仍然是药价治理的关键,政策将集中在对处方的管理上,通过药品比价推动用户向低药价渠道流动,从而降低统筹资金在门诊的消耗。不过,药价治理最终还是需要回到医保支付价,医保支付价全面实施后,用户会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决定使用什么类型的药品,最终将抑制高价药的销售能力。